【征文】小学时的刘老师才华横溢,还会结婚时的“回车马”……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当这首充满年代感和青涩回忆的《童年》响起,那个曾经满怀凌云之志的少年凝视着黛青色的天际,小学生活的温情瞬间如放电影般逐帧浮现在眼前。
我记得上三年级时,任教语文的是刘老师。记忆中的他相貌英俊,身材高挑,尤其是他那富有旺盛男性荷尔蒙的络腮胡格外引人注目。
刘老师是我们本村人,师范毕业后留在村小从教,他才华横溢,口齿伶俐,社会阅历相当丰富。当时我父亲任校长,刘老师跟父亲过从甚密,我跟他就没那么生分了。
零几年的教师工资较低,常常是捉襟见肘。因此刘老师除了教学外,还要营务庄稼。他来上课,身上总带股让人亲切又熟悉的泥土气息,公尺布的裤腿上总沾有黄生生的泥点,黢黑的指甲缝里透显出常年劳作的痕迹。对于我们今天具备卫生意识的人来说,或许这种“不洁”总让人难免产生些微嫌恶,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觉得这种“不洁”是发乎自然的、平易近人的、淳朴可亲的,正如他那口带有浓重乡音的“镇普话”一样。
刘老师除了教学成绩出色外,还精通我们镇雄人结婚时的“回车马”。那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是两厢情愿后直接去婆家,并未大操大办。只有在当地德高望重、条件优渥的人家才办得起。
那次,我记得是我们村的支书家接儿媳妇,刘老师的伶牙俐齿早就尽人皆知,于是被主人家请去“回车马”。“回车马”是我们镇雄历史悠久、流传至今联姻的重要仪式和风俗习惯。我跟着父亲也去了,具体的场景记忆比较模糊了,但当时刘老师回车马的说辞我还记忆犹新,因为事后我特意央求他说给我听过多次:“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到此,车马还乡。一张桌子四角方,张郎设计鲁班装。四方雕起云牙板,中间焚起一炉香。到香得香,灵宝会香。香插三炷,片请十方。一张纸钱白如银,烧来回送车马神。娘家车马请回转,婆家车马出来迎。天煞归天界,地煞入幽冥。天无忌,地无忌,年无忌,月无忌,日无忌,时无忌。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百无禁忌,大吉大利。”
刘老师不仅熟悉农村婚俗,而且遇事沉着冷静,育人有方。有个春季学期,一位讨人嫌的同学交了白卷,上面还赋诗一首:“小子本不才,爹妈逼着来,白卷交上去,红蛋滚下来。”刘老师当时并未大发雷霆,他镇定自若的说:“响鼓不用重锤敲,你读书是帮你自己读,别在该努力的年纪选择安逸,也别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几句话让那位同学羞红了脸。
我那时特别调皮捣蛋,父亲在校会上三令五申不许说脏话,可我置若罔闻。一次课前我高声说道:“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我是你家老干爷。”不承想刘老师已经站在我身后,轻抚着我的后背,我忙转身,刘老师捏着我已经通红滚烫的脸蛋,用严厉的口吻说:“你的辈分还大得很,不许说脏话,要学会文明礼貌。”
课堂上,刘老师除了教授书本知识外,还时不时的说几个蕴含生活气息和农人智慧的“东猜子”给我们猜。“空筒树,闪枝丫,又结梨子又结瓜,又结苏州毛板栗,又开云南二省花。猜一种农作物。”刘老师神情温和的刚说完,原本像霜打的茄儿一样无精打采的同学们瞬间神气活现,精神亢奋,个个都抓耳挠腮、窃窃私语,刘老师见活跃气氛的效果达到了,神秘莫测的说:“荞子啊,我们平时烙荞粑粑吃的荞子啊。”
我们的小学生活之所以让人留恋难忘,是因为那份纯粹而简单的快乐被时光洪流席卷而去了,是因为曾经那个拢鼻子、玩泥巴的少年韶华不再,如今的脸上多了几分岁月的沧桑和隐秘的忧郁,是因为那束清澈明亮的眼神已经被生活的尘埃稀释了,变得黯淡无光。岁月流转让我“盼望早点长大”的梦想如愿以偿,却把那个天真无邪的自己遗落在了时光深处。
【学生家长采访视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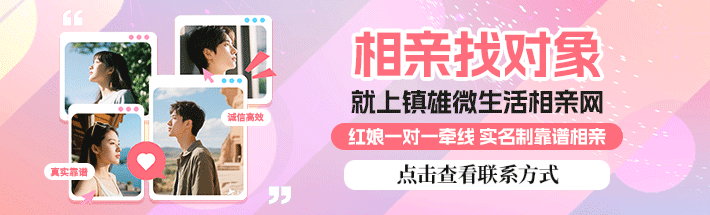



 游客
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