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等一回!赤水河"花鱼"洄游!
来源:《昭通日报》、@镇雄融媒
原标题:“从传说洄游赤水河,你们终于又见到我”
一条“花鱼”的自述
——从传说洄游赤水河,你们终于又见到我
《昭通日报》2025年9月15日第3版版面图
当阳光穿透赤水河的波心,在深水区的幽暗之中,我能感知到水流细微的脉动。那些微小生命在水中穿梭的震颤,岸边芦苇轻拂水面的低语,甚至远处桥上人们惊喜地指点和低呼——所有关于生命与守护的故事,都沿着水流,涌入我这条“花鱼”的感知。
我是金沙鲈鲤,赤水河曾经的王者,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大花鱼”“花鱼”。我们身披如星光般的黑色斑点,曾令无数人为之倾倒。幼年时,我们如泥鳅般灵动,常贴着河岸觅食;成年后则遨游于敞亮的中上层水域,行动迅捷如闪电,生性凶猛。3岁时,随着生命走向成熟,每年2—4月,我都会循着血脉深处的召唤,逆流而上,将生命的种子播撒在上游激流的白沫与喧嚣之中。
在赤水河里,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水中老虎”。
(一)
记得那个距离赤水河源头仅5公里的贾家坝河段吗?那里活跃着我的口粮——桃花鱼群,它们轻灵如穿梭在水中的幻影。再向下游20公里,在倮倘落水洞神秘的暗河深处,则隐藏着我和其他五六种伙伴的身影。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的工作人员最熟悉我们的踪迹。
在深水区游弋时,我总能感应到岸边人兴奋的目光。2021年那个平凡的日子,鱼洞河段的护河员姚明昌正对着水下监控屏察看,突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唤——他认出了我。那声音里饱含难以置信的颤抖:“30年啊……自从看到一条尾巴耷拉在尼桑车外的大花鱼之后,我就再没见到过活生生的你们了!”监控镜头下,我矫健的身姿在清澈的深水中从容掠过,这久违的照面,穿透了漫长时光的阻隔。
你们人类口中那些被称为“花鱼洞”的地方,正是我们族群曾经的王国。41岁的护河员杨世发站在赤水河香坝河段的花鱼洞岸边,向我讲述他的哥哥们年少时的辉煌战绩:“我10岁那年,他们就在这洞口捕到了一条六七十斤的巨物,银鳞黑斑,威风凛凛!”石坎河岸边的村民王世东也充满怀念地补充道:“河流深处连着暗河,那些年,洞里常冲出大鱼,其中就有你们大花鱼。”这些地名如烙印般镌刻着我们的兴衰。
在赤水河斑鸠井大桥头,村民郑祖萍倚栏眺望,话语中带着欣慰:“如今站在桥上,天晴水清时就能看见鱼群嬉戏。大花鱼喜欢待在深水区,用水下探头一照,就能发现它们。”虽然在水底,但我能清晰地感知到她温柔的目光无声地拂过河面——那是人间最温柔的探照灯。
更让我动容的是镇雄纳支寨的彝族汉子徐国勇。当别人好奇地问他是否吃过大花鱼时,他连连摆手,神色凝重:“大花鱼是我们彝人的图腾之一!我们怎能吃它?”这份源自血脉的敬重,仿佛一股暖流流经我的鳞片。赤水河畔,我们与人类的故事,不仅关乎生态,还深深植根于一种古老而鲜活的文化图腾之中。
西南大学水产学院副教授刘建虎道出了我们的生态价值:“大花鱼即金沙鲈鲤,是赤水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指示性物种,更是旗舰种与指标种。”我们种群数量的起伏,正是这条河流脉搏最真实的记录。
工作人员开展日常监测。
(二)
这份记录曾触目惊心。20世纪90年代后,拦河筑坝的轰鸣、浑浊刺鼻的污水、贪婪无度的渔网将我们逼向绝境。在赤水河(昭通段),我一度沦为老人们口中的传说,连“罕见”都成了奢望,唯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模糊的记忆碎片证明过我们曾经存在。
为扭转赤水河病态的喘息,还我们一个“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世界,一场破釜沉舟的拯救行动拉开帷幕。2005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运而生。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流域正式启动十年禁渔,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坚定地接过了守护的旗帜。
希望的种子在长江十年禁渔的第二年便悄悄萌发。2021年,赤水河云南段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金沙鲈鲤重新被捕捞记录在册!其中一条体长已达24厘米,对近年来的发现而言已属可观尺寸。这微小却坚毅的信号,表明我们正从“稀见种”艰难地向“偶见种”回归,族群的生命力正在顽强复苏。
2023年,捷报更加密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飞博士带队在不同河段采样监测,均成功捕获到我们的身影。刘博士特别提到:“9月,在上游支流妥泥河也采到了金沙鲈鲤。”这是我们的生命版图在悄然扩张,如同枯枝上悄然萌发的新芽。
2025年6月14日,晨曦微露。赤水河云南段小三峡江面薄雾轻笼,巡航的游艇划破宁静,驶向河道中央。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与西南大学开展的联合监测开始了。“起网!”“起笼!”随着渔业站许全伟站长洪亮的吆喝声,银鳞跃动:光泽黄颡鱼、白甲鱼、泉水鱼……纷纷入桶。
如今,赤水河中的生命交响已从2020年的36种增至44种。华鲮新晋上榜,为这首乐章增添了新的音符;我们金沙鲈鲤与岩原鲤等曾经的稀客,如今已能时常现身;大花鱼等肉食性鱼类的重现,标志着河底一度断裂的食物网正在被重新编织,并逐步趋于完整;四川白甲鱼等“故交”的回归,更是水质稳步提升最有力的生物见证。
鱼类专家们凝望水面的目光虔诚而专注,他们的每一次下网、每一次采样,都是对河流生命脉搏的深情叩问,都在为赤水河不可复制的生命网络编织着更为牢固的未来。八载禁渔守护,赤水河的脉搏从未如此强劲而清晰,如同一条正在苏醒的巨龙在云贵高原的怀抱中舒展筋骨。
工作人员开展日常监测。
(三)
当夕阳的余晖为赤水河镀上金边,我感知到来自岸上另一个“虎之族群”炽热的目光。溯流而上至镇雄县果珠彝族乡,高坡村深处藏着一处世外桃源般的村寨——纳支寨。在彝语里,“纳支”意为亲密无间,由“纳”(手)与“支”(手指)组合而成。寨子最高处,两座古老的烽火台如同忠诚的卫士,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和蜿蜒流淌的赤水河。
纳支寨的美曾引来敌人的觊觎。清同治年间,一伙悍匪将寨子围得水泄不通。彝族同胞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筑起屏障,最终令土匪铩羽而归。自此,四邻八乡无不钦佩地竖起大拇指。“纳支”的意蕴也由此升华,成了了不起的象征——如同我们大花鱼被冠以“水中老虎”的美名。
在这里,彝族的红、黄、黑三色文化在广场上熠熠生辉:黑色象征深沉的土地,是生命之源;红色代表燃烧的火,寓意驱散黑暗的勇气和热情;黄色如同温暖的阳光,意味着永恒的希望与光明。远处的飞鹰雕塑与广场中央威猛的老虎图腾遥相呼应。彝族汉子徐国勇的话语铿锵有力:“大花鱼是我们彝族人的图腾之一,我们绝不能吃大花鱼!”那份源于血脉的敬畏与守护之心,如赤水河水般清澈而坚定。
对彝人而言,“虎”是刻进血液的图腾,“我骨是虎造,我血是虎造”的民谚便是印证。在这片以虎为魂的土地上,作为赤水河的“水中老虎”,我——金沙鲈鲤,何尝不是承载着彝人精神图腾的鲜活象征?这份跨越物种的默契,构成了赤水河生态保护最深沉的文化基石。
纳支寨始终传承着勇猛精进的“虎魂”。新时代的彝家儿女,身着火红盛装,银饰叮当,笑迎八方来客。男子拨动月琴,歌声与美酒交融;女子舞姿翩跹,热情似火。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垂髫孩童,在直播镜头前、抖音画面里、微信朋友圈中,自信地展示着古老彝寨喷薄而出的生命力。他们传递着彝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也传递着对这条与我们大花鱼共生共栖的赤水河绵长的祝福与坚定的守护。
他们更深知,只有碧水长流、鱼群欢跃成为日常,我们这些“水中老虎”与岸上虎族图腾的传说,才能在赤水河的脉搏里真正实现永续共生。
夜色如水,温柔地浸透着赤水河谷。我游过花鱼洞口那片熟悉的水域,幽暗的洞口仿佛亘古的凝视。不远处,纳支寨高耸的烽火台在月光下勾勒出刚毅的轮廓——台上彝人那斑斓的猛虎图腾,似乎正与深水之下我的脊背隔空相望。
虎啸山林,我御深流。两种“虎”,在不同维度守护着同一条河流的血脉与尊严。禁渔令如同八年不辍的春风,终于唤醒了深埋河床的生命火种。当我们这些“水中老虎”重新在赤水河深水区展露行踪,当猎食者的身影再次串联起食物链的完整循环,赤水河便找回了它失落已久的野性心跳与内在平衡。金沙鲈鲤的“虎”踪所至,正是赤水河生态韧性最雄辩的证词。
俯瞰纳支寨。 记者毛利涛 摄
(四)
在赤水河的守护者心中,我们金沙鲈鲤是他们情感的寄托与行动的坐标。赤水河香坝河段,护河员杨世发的身影早已成为岸边一块移动的界碑。自2016年肩负起生态巡护的使命以来,这段河流和其中的生灵便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
沿河岸行走,他能准确指出每一处鱼儿的庇护所:“下面那个回漩涡,是鱼儿停留歇息的好地方,但也常常吸引捕鱼者。”岸边樱花和李花的芬芳,也无法掩盖他曾收缴百余件渔具时乡亲们不解的怨言。记忆里,少年杨世发也曾是捕鱼好手。然而禁渔令如同惊雷,让他幡然醒悟:“鱼也是有生命的,它们也需要被保护。”从此,守护的责任融入了他的本能。河畔的庄稼默默地见证了杨世发的付出: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巡河的路上。
离花鱼洞百步之遥,杨世发驻足于一个幽深的洞穴——麻柳洞前。他回忆起2024年盛夏的那场暴雨:“洪水裹挟着几十斤鱼从洞里冲出,鱼儿身上沾满淤泥,村民们提着桶蜂拥捡拾。”他第一时间拨通镇雄县公安局大湾派出所电话,以人身安全为由坚决制止了这一行为。麻柳洞的传说在村里口耳相传——据说其幽暗深处可通以勒,但从未有人真正走通过,更为它增添了几分神秘。
行至深水洄流区,杨世发的语气变得温柔起来:“看,这里有一对红鲤鱼,只钟情于此地,总在麻柳洞和花鱼洞自在游弋。”花鱼洞,曾是我们族群繁盛的中心,也是杨世发情感的密钥:“我的哥哥曾在这里捕到过一条巨大的鱼,那震撼的场面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那年我才10岁。”
他尤其珍视花鱼洞,因为这里不仅是鱼类的故园,还是他与水中生命缔结情谊的圣地。他笃信鱼儿亦有灵性。2023年,他将一条娃娃鱼(大鲵)亲手放归花鱼洞。这生灵竟记住了他的脚步与呼唤。此后每次巡河经过,杨世发总要入洞探望。每每听到他独特的声音,娃娃鱼便如老友般从幽暗中缓缓游进浅水区,坦然相对。若有他人同行,任凭杨世发如何呼唤,娃娃鱼始终深藏不露,宛如一个怕生的孩童。
杨世发与鱼的牵绊远不止于此。同样是在2023年,当他把娃娃鱼放归花鱼洞后不久,有村民在对岸发现了一条全身是伤、脚部溃烂的娃娃鱼。杨世发的心猛地揪紧,急忙赶去。目睹惨状,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如包裹婴孩般将其小心抱起。经请示后,他毅然将其带回家中救治。
“治好它的伤最要紧!”望着在盆中扭动挣扎、无比惊恐的小生命,杨世发既心疼又无措。他四处求助管护局的同事,翻遍相关书籍寻找救治方法。最初上药困难重重,他只得唤来孩子帮忙:一个投食安抚,一个专注涂药。经过半个月的悉心照料,娃娃鱼的伤口渐渐愈合,它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下来,虽仍渴望赤水河的怀抱,却已在这方水盆中寻得片刻安宁。夜半时分,娃娃鱼凄清的鸣叫一度扰得孩子难以入眠。杨世发唯有将心比心地解释:“它疼啊,就像你生病时一样难受,我们忍一忍好不好?”
最终,这条娃娃鱼带着杨世发一家温暖的印记,重回赤水河的怀抱。
作为河流的哨兵,如何保护好金沙鲈鲤等生灵的守护者,杨世发内心的忧虑如同河底潜藏的暗流。巡河途中,看见那些被农人遗弃在岸边的农药空瓶,忧虑如阴云爬上他的脸庞:“这些残留的液体最终都会流进河里。” 他最大的心愿朴素而深沉:让赤水河的生态回到他儿时的模样——那时,巨大的珍稀鱼类如同河流的魂魄,在清澈的深水中自由游弋。他默默祈祷着我族壮硕的身影,能再次穿梭于花鱼洞幽深的水域。
崖上石寨一角。记者毛利涛 摄
(五)
赤水河正在复苏,而我们花鱼的洄游,恰如它重生的心跳。当渔业专家的监测船划开金色的波光,当护河员杨世发向花鱼洞投去关切的目光,当彝族汉子徐国勇肃然声明“大花鱼是我们彝人的图腾之一”,这条河流的命运便与人们的信念紧紧交织。
花鱼洞的传说不再只是尘封往事,麻柳洞暗河的低语也不再是惊鸿一瞥的偶然。渔网收起的不只是数据,更是对未来的郑重承诺。我们这些回溯赤水河的“花鱼”,身上斑驳的不只是自然印记,更是人类选择与自然和谐相处、再造生机的见证。
站在纳支寨高耸的烽火台上,赤水河在脚下蜿蜒伸展。彝族少年的眼中映着粼粼波光,或许其中正闪动着我矫健的身影。从传说到现实,从稀见到偶见,终至繁盛——在这条河流的复兴史诗中,每一个生命都找到了自己的应许之地。
我在清流中游弋,我的斑点是赤水河重生的印记,我的每一次摆尾都是对守护者最深的致意。
远眺赤水河流域——绿水青山奏交响。记者毛利涛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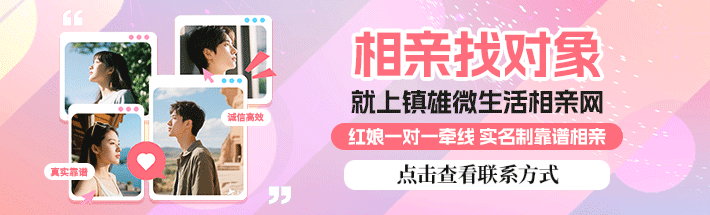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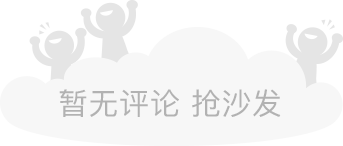
 游客
游客



























